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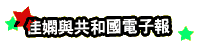

文/鯨向海
我在某年冷氣團大軍於此城市盤旋不去的聖誕節,認識了身穿火紅大衣的楊佳嫻,那像是一個駕雪橇帶來歡樂的人,「此刻我神情鮮豔/億萬條微血管都酗了酒」,餽贈給我許多熱情和詩意。她自小就是個文藝青年,四處參加文藝營為生。我此生唯一參加的幾個營隊裡,她也在其中,只是當時我們並不認識。雖然如此,我還是忍不住問她:「當時是否注意到我?」她大笑幾聲,用巨大溫暖的眼神瞪視著我,然後認真地說:「你那時非常年輕。」這就是我們神秘而不可理喻的默契了。
我的詩和佳嫻的有本質上的差距。她心裡有幾個文學上的典範,都是博學有才氣的人物,她常在自己的網站上為詩為文不斷向他們的文風與人格致意。我則偏愛一些野生的想像,創造力層出不窮的魂靈,而那往往還沒成為典範或者抗拒著所謂典範。她詩中的自然經驗大部分和過往的詩文傳統是一致的,她選擇用以訴說或者暗藏情緒的事物,如「窗口」、「雨聲」、「沿岸」、「星座」、「月光」、「經書」、「門」等等班底,我們並不會感到奇異陌生。繼承了詩國度裡,諸位意象與美學帝王們的年號和皇旗,她的血統顯得格外正派光明,總是有些驕傲地說:「為什麼那些大詩人寫過的題材我就不能再寫?」。然而那些已經在文學集體潛意識中長滿灰塵的意象,經過她纖纖玉手敲打入新科技的媒介中,便嘖嘖地重新發出了奪目的光輝,這是她的天賦她的本事。又或在詩中的小說課堂上冥想魯迅,或者幻想自己如細雨穿越李賀的房間,或和蚩尤一同混跡於動物與鬼神之中,凡此種種:「你乾涸的哭聲內包著果核/哽著我閱讀的喉嚨」,詩彷彿她與各類經典重新發想與對話的講堂書院。她推崇楊牧所說「應景應制的東西,我想不是我們在追求的」;而必須是穿越時空限制的「永遠的現代詩」。她自己也曾高歌:「我們既漂泊又安定/坐如魚而臥如雁/在經典中腹語」。
然而她卻明明是個通曉時下流行文化的傢伙。她的詩固然鮮少出現手機,名牌或者PUB等等事物,天曉得她評論起這些現代性配備,卻是熟極而爛的大行家。有次前往某高中名女校評文學獎,平日嘴裡盡是菁英文學的她,眼望著底下無數充滿夢想的少女們,當下引用起流行歌手的歌詞作為巧喻,一時正派文學與大眾通俗文化共冶一爐,讓那些初入文學殿堂的年輕心靈為之激動不已。有時聊到酣處,我也會狡獪地建議她寫些貼近搞笑人生展現本性的題材,譬如統聯客運上的有趣廣告或者KTV包廂搶奪麥克風的事件等等;她總是熱烈地響應但從來就沒有真正完成過一首。她的詩世界隱隱然有著不容侵犯的美學秩序,那些宿命般必然與現實生活相互抗衡著的人文構思,恐怕連她自己也難以控制地繁衍成一處純然形上的精神場域。這可以對照她所說的:「讓嗜字者持續書寫的最大動力就是可以讓我們在現實的城市之上,按照自己的藍圖建造另一座炫麗的精神城池。」。
佳嫻愛說自己是嚴肅苦悶的,儘管常常搞笑,像一個臨時喜劇演員,但內心潛藏著諸多莫測的哀感傷愁,而她敢愛敢恨的性格,造就了她「愛與哀愁同等獨裁」的詩帝國。其中既遵守著天生麗質的文字品味和經典教養,也同時用鐵鞭、鐵鎚和匕首馴服著讀者;這是她巨大的文明所以令人屏息:不管是「一些思想在鴟梟裂鳴中驚起」的大子夜歌型,或者像是「直接以誠實的頭骨向痛苦行禮」的暴力華爾滋類,讀之都是讓靈魂七步見血的心驚。「而我們耽溺於暴力/最初的夢被對折再對折/無聊或者死亡/享受悲劇的樂趣」這裡的暴力,是對她心目中的美學與理想國度的開疆拓土所採取之攻略手段;乃一種以暴制暴,抵抗外在世界的無聊與衰朽的必要之惡。我有時會以為她的文學品味未免太過專斷獨裁,但或者就是這樣高蹈絕對的美學傾向,使得她的作品風格出眾,而她顯然也因此充滿了高度的自信。
而佳嫻的情詩,是一處期待著絕對敏銳與領悟的戰慄美地:「讓你看見我變成一滴未融的霞色拋向/宿命的銅杯」。那隱喻的核心似乎總是拒斥著「不懂愛」或者「不會想像愛」的讀者的;每一首情詩光熱的目的都是為了不偏不倚抵達那個唯一的「愛人讀者」的內心。其中容攝了情感的百般樣貌,忽而豪壯如「我是脫掉了戰甲的雅典娜」,忽而溫柔地訴說「最寒冷的時候,你把我摺起來/像一方小小的手帕/放在胸前的口袋」;堪堪成為當代最完整的戀愛教戰手冊。但我們若只是被那松木如塔中研究羽毛的少年,或紀元消逝後重啟愛情信史的革命軍等種種臨床徵狀所迷惑,必然會忽略底下暗藏的另一層「哀愁」的病因本質--那知識份子式的,屬於自傲信仰與獻祭儀式的「隔著海,我們靜默地喊話/像怎麼樣都無法穿破濃霧的光束」。於是「時間的易逝」與「小眾的孤獨」成了最重要的命題,那是〈時間從不理會我們的美好〉(此詩借用羅智成的詩句為題),也是「我們美好的連神都忌妒」的勢單力孤。在許多首詩中,長期被聲嘶力竭呼喚著的「我們」,除了解讀為「以石子沉沒於江心的快感/我們的見面充滿慾望」那類情愛關係,更像是幻想中一群思想契合的族人:「當暴雨季開拔了八百哩/我們乞求唯一之身形……天秤兩端,我們是/等重的鐵與棉花」。〈雅教斷簡〉一詩中她將自己的處境自比為文學貴族,藉著那些宮殿與儀典的追索,發出「優雅是唯一的宿命」的豪語,可說是這種「怎麼可能沒有怨怒呢」之「哀愁」的全面爆發。
這是佳嫻的第一本詩集。從她生平的第一首詩那個歌頌「春天的裙裾」的中學女孩,到1998年在網路上貼出第一首詩那個說「我的夢還很瘦,哦是的/甚至可以穿越過現實的牆壁/穿越過那些灰色的雨滴而不被淋濕…」那個大學女生,這其中多少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意味。事實上早在一年前,她就已經完成了第一本原生詩集,那個版本和現在呈現在各位讀者眼前的這本,又毫不容情地砍殺了更多她所謂的「少作」。她曾經在一篇應邀書寫對同輩詩人觀感的文章結尾中提到:「我很喜歡『我們』現在的狀態,在閱讀和觀摩中摸索,震盪,對於前世代的美學和知識非常注意,但也不放棄探尋新的突圍方式。較令人焦慮的,可能是時間感的加速,比如過去的詩人可能十年轉一風格,而大量利用網路發表與寫作則使得寫作速度和量都提高,但讀者胃口大,天天上網瀏覽,如果這三個月的風格都頗相類,就會被指責沒有進步……」。「風格」是每一個世代的詩人永恆的焦慮。從早先我在她那本自製詩集中的序寫道「此詩集乍看歌舞昇平,其實飛花墜葉皆可傷人,希望過路人等閱讀小心」,到近幾月她寫詩的速度變得緩慢,作品也顯得沈穩,比之往昔的「鍛句」,現在更要求「境界」(這些變化後的作品大多數收錄於此詩集卷四中)。
我們可以理解在她經歷過這麼多暴雨如銼的艱險書寫之後,想要追求的一種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地,如她說過的:「我很不願意把思考和書寫一直停留在對於宏偉事物的自我想像,那些炫麗的修辭,不足以表達真正細密的情感千萬分之一;即使我從很早就體會到,作品動人的力量來自於樸素的心靈,讓情感從裂縫湧現,而非自己替它妝點,仍然放任自己製造了太多浮麗而壯觀的假象。有時候,僅僅是誠實地寫出一連串動作,或者是讓眼光游移的動線層次浮現,就具備了巨大的情分和幽微的空間感。」但如此迅速地跳過青春時期的狂放銳氣,而直接來到了女皇攬鏡沈思的暮年,這「生理年齡」和「詩思年齡」的過大差距,是否還有可以斡旋、辯證的餘地?比較分別寫於2000年和2002年的兩首同名的〈原諒〉,兩年前在詩中忿忿地訴說「變動過的板塊永不癒合」、在陰影下見證靈魂的巨大割禮的拾骨者,而今變成了靜靜「看白鷗沿海岸線逸去/藤蘿翻過舊欄杆」,默默地「吹滅了燈火,回到各自星宿」的某人;此其中風格的轉變正是「彷彿午後看著/光從右頁移至左頁/那樣遙遠」,那是心境上的也是境界上的,孰優孰劣,不同的讀者或者有不同的偏好吧。如果讓我來當編者製作一本楊佳嫻的詩集,那應當是不同的風貌,譬如我可能不會捨棄像是這樣更年少的楊佳嫻:「金色城池般的魏晉啊 / 也慢慢溽濕起來」或者「馬車正在融化 / 我必須以更緩慢的速度 / 等待一個充滿南瓜與老鼠的樂園」。
《天龍八部》裡,當虛竹背著天山童姥為了躲避李秋水跌下萬丈深淵,卻意外地被慕容復的「斗轉星移」一送,被段譽「凌波微步」一頂,因之毫髮無損;只聽得童姥有些驚愕地喃喃道:「數十年不下縹緲峰,沒想到世上武學進展如此迅速。」--那思路萬丈深淵的旅程,本毋須言說和表態的累贅;這古遠的讀者和詩擁抱的過程一向進行得如此艱險。我在此代替佳嫻說出她的期盼;但願某個世代某個時節交錯的瞬剎,能巧遇傳聞中功力高深的知音者如詩中的天山童姥,給予一切詩學修為正義且體貼的評價。只因那躲在暗處不斷鍛鍊劍術和掌風的作者之神,永遠比這個鮮少讀詩意願的世界,更加苦悶、更加羞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