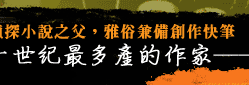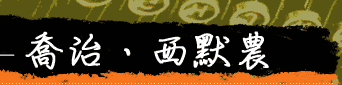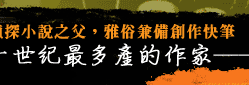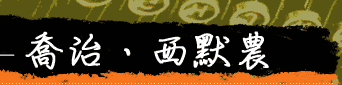| 二月21日晚間七點在FNAC法雅客文學咖啡舉辦座談會「給我一杯黑咖啡──傳奇作家西默農與他的探長馬戈」,正是值作家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百年冥誕全球百年紀念版問世之際。木馬文化以馬拉松長跑的準備心情,為台灣讀者引介這位享譽世界的大師作品,第一波的兩本新書《黃狗》和《屋裡的陌生人》,特別邀請淡江大學吳錫德副教授、知名作家韓良露及盧郁佳共襄盛舉。
快與繁
 吳錫德首先提到出生於比利時列日的西默農由於作品主要發表於法國,故可謂一個「法國作家」,法國文化界今年亦盛大慶祝他的百年紀念。作品流傳遍及整個法語區的西默農是個寫作快手,當時甚至有人為想親眼目睹他的「快」願意出錢請他在二十四小時內於大街上公開寫作。小說作品多達406部,說西默農是著作等身實不為過,因為以一本書一公分計算都可以有四公尺了。他另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生命中曾和兩萬多個女人有過性關係,如以盛年六十年來計算,平均不到一天就有一個女人。
吳錫德首先提到出生於比利時列日的西默農由於作品主要發表於法國,故可謂一個「法國作家」,法國文化界今年亦盛大慶祝他的百年紀念。作品流傳遍及整個法語區的西默農是個寫作快手,當時甚至有人為想親眼目睹他的「快」願意出錢請他在二十四小時內於大街上公開寫作。小說作品多達406部,說西默農是著作等身實不為過,因為以一本書一公分計算都可以有四公尺了。他另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生命中曾和兩萬多個女人有過性關係,如以盛年六十年來計算,平均不到一天就有一個女人。
Savoir-vivre的探長
西默農小說的主要對象都是下層階級。而探長馬戈也非一般辦案型的探長,用法文來形容,馬戈是個savoir-vivre(懂生活)的探長,馬戈探長是靠一點靈光、啟示,從事件氛圍中找到破案的蛛絲馬跡。他小說中常出現美酒美食或是描述氣味的文字,借用飲食內容即可知道這個人的階級與出身背景。
偵探兩大家族
「閱讀推理偵探小說時,這些小說的作者就如同是讀者的朋友一般」,韓良露感性開始。她認為偵探小說可以分為兩大家族,一是從1890年到1920年的古典黃金時期,日本人稱此時期為本格派,此階段注重推理小說本身謎題的設計和偵破命案的方法,是個科學辦案、講求證據的時代;而且故事背景在上層階級生活圈,主角來自上層階級,裡頭的探長都是業餘探長,讀者從不知探長何以為生,如白羅、馬波這些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所創造的偵探都可名之為「搖椅上的偵探」。
西默農在1930年代樹立的馬戈探長,則開啟了另一偵探家族的新篇章。馬戈探長這一回可是貨真價實的警探,有務在身。然而身為警探就不可能代表資產階級,頂多是個中產階級。接著就是小說背景脫離了前述偵探家族喜用的莊園、東方快車、尼羅河遊輪,而來到了市井的咖啡館、暗巷之中,因為一般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親臨一次東方快車或豪華遊輪的。他的馬戈探長成了家族之後如漢密特、錢德勒等人小說發展的原型,相對於總是乾淨優雅的白羅、福爾摩斯、馬波等探長。
大眾文學的旗手
追根究柢,西默農可以在創作上如此多產並且廣受讀者歡迎,其實有跡可尋。多產,除了無庸置疑的乃西默農本身的天分,另外得以解釋者則為「時代需要」。在1930年開始,出版傳播業走進它的黃金期,印刷業的技術改革帶動了出版類的商業契機,報社出版社紛紛創立、讀者廣增,一個前所未有的市場鼓動著西默農的創作因子並需求著他的寫作速度。西默農的出生地列日也陶塑出其複合性格──一方面帶有拉丁式的熱情,可以源源不絕採擷靈感;一方面又帶著如清教徒信仰般的規律寫作節奏,故得以造就我們今日所識的多產印象──,列日此一城市融合了荷德條頓語系和拉丁法語兩種,一冷一熱的民族與語言浴化出大作家的兩樣風貌;尤其讀其小說更可以感受出其中馬戈的冷靜性格,能沈著觀察事件相關的人事物,而同時他卻又以著易感的、羅曼蒂克的心腸在觀視這些人物。
西默農的小說特質
盧郁佳認為西默農這位離我們年代較遠的偵探小說家,無法以加法減法來分析,他的文字有一種非常貼近讀者的現代性。
他的故事沒有錢德勒華麗,錢德勒的小說就有如張愛玲的一樣,舖排華麗、場景鮮明。但西默農沒有這麼做。西默農的情節進展快速,人物一個個接續地丟出來。西默農不像卜洛克,他的小說裡不太有機關佈景,不會在片頭時嚇你一跳;他沒有鐵伊的犬儒主義;他更不是米涅.渥特絲總是憤憤地要伸張社會正義。西默農的小說就像張愛玲描述自己的小說:裡面沒有大奸大惡,只有小奸小壞。是日常生活的平凡人沒有存心、單純一個小小私心或差池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命運。就像張愛玲說的「霧樹霧樹」,就是一個人衣服脫下來之後所聞到的袖口的體味,那裡頭有人的清淨。它並非美麗到會讓你感動得流下眼淚的溫馨的事情,而卻是在不可挽回的錯誤後,你會「啊」地發出一聲嗟嘆與同情。在那結尾,你心上一陣紐絞「當時他不如此就好了」的惋惜,那是一種接近我們對自己的與對別人的人生情節的感情。
偵探家族個性
現在台灣讀者所熟知的幾位偵探小說,其實就是作家本尊化身。比如錢德勒,就是個花花公子大哥。他出場時衣著華麗,似乎每日都有一個Party可以參加,底下的人物妝扮如時裝秀一樣。他極盡類型美學的極致──蛇蝎美女就必然有一副蜜糖似聲音,放電時讓人渾身舒軟;如果是金髮小天使,腦筋不清楚的美少女,就代表著災禍的根源。比如卜洛克,他是心碎的小流氓,瀏海斜披臉前,貼心的幽默中帶有溫情的心傷,小流氓在酒吧點一杯酒,臉上寫著「我需要愛」。比如說鐵伊像是大媽媽,類似佘太君那種,你的戀愛對象不合她意,她可能會拿龍頭柺杖打你。
而西默農,則像是爸爸。沒有太大的能見度,在現實中失去存在感,但對發生的一切似乎又了然於胸,一切在老爸心中已有定見,雖他偶爾難免出紕漏。而且由於父性形象,所以我們的探長馬戈並非極具性吸引力或是性格上有特殊魅力的一型。馬戈,比較像公務員,對自己的工作競競業業力求完成,對服務的對象有一定的情感,他的出場從沒有太多的自我表演、或是要故設陷阱地去釣兇手,沒有,馬戈就是個老實人。小說作者西默農沒有耍花俏招數,就只是老實本分地走向結尾,雖其過程中仍不乏偵探小說必要的機關,而且算來驚奇意外一樣不少,而西默農這「一樣也不少」的特性,就非常符合老爸的個性──出門前萬事皆備。就好像高級房車,穩定!舒服!安適!當年朱德庸的漫畫可以如此常年連載,是因為他成功地把人物類型化,並在四格的起承轉合中帶給讀者可預期的舒服的閱讀感受,可以說作為一個多產作家的必備特質就有如具備高級房車的特質。
類型的純粹
西默農不像綾十行人。綾十行人深入偵探類型,喜歡在敘述、意念上玩遊戲,他想當偵探小說的類型研究者甚於情節的製造者,他寫很多種小說,犯罪、言情小說……。可是在一個生態環境裡──推理偵探小說界也是──類型分化也就是類型的純粹是作家進化的原則,而不是集合驚悚、懸疑、奇幻、社會批判……於一身像《哈利波特》。西默農的小說,就謹守在偵探世界裡面,讓你看到偵探小說的好處,這一點亦非常符合老爸腳踏實地的作風。西默農的小說不會像其他的偵探作家有許多的歧出與意外,他有應該有的意外但沒有不該有的意外,事件的的兇手絕不會天外飛來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高級房車的穩定,從不會讓買家對任何一期的馬戈辦案有失望、「了錢」的想法。
小說運用的元素──找不到出口的無罪者
韓良露提到,西默農喜歡用「出口」這種說法,他認為許多人在生命中找不到答案,即找不到一個出口時因此才犯下了罪,所以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犯罪者」,只有找不到出口,或是找錯了出口的人。
一般的偵探小說往往在結局之後你仍不會豁然開朗,面對作家的情節安排讀者常常都是猜錯的份,可是西默農的小說不玩這種遊戲。備受柯蕾特、紀德、霍布斯邦、林語堂等名家所稱贊的他深諳小說書寫的重要元素,風格簡潔明快,充盈詩意的簡單文字具穿透力,讀到的人無一不深受觸動,而這不是福爾摩斯系列有的特質。所以讀到《屋裡的陌生人》結局,盧爾薩一個人獨自坐在酒館,面前一杯紅酒的文字收尾,我們竟還是那麼好奇故事中的律師後來的發展如何。西默農的元素就是他對人生的領悟,而這領悟在小說結束之後遠遠超越了情節,《屋裡的陌生人》正涵藏了這種人生小說的元素。盧爾薩律師的人生曾遭受打擊,他二十年來壓抑在暖爐、勃艮第酒與自己的書房和書本之中,一天一個陌生人死在家中後才重啟他的人生大門,他藉著調查事件原委外出到睽違二十年的鎮上,才發現自己這二十年來在人生上的缺席。表面上的調查兇手可是實際上卻是在調查自己的人生,盧爾薩正是那個找不到出口的人;而小說中的兇手因嫉妒而殺人,則是一個找錯了出口的人。西默農的另一部作品《雪上污痕》,便如同是《罪與罰》普及版,其中亦處理了對生命的重要領悟;而《黃狗》,如同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被污辱者與被損害者》,將黃狗這生物與視覺意象──狗的忠實──與故事主角的過去結合,象徵了人的「Age
of Innocence」(純真年代)。
馬戈探長是西默農的理想化身,馬戈的感性、溫純、善良正恰恰相對於西默農。西默農,如果要類比的話,就像畢卡索,兩人同樣在世即享有盛名、榮華富貴,他們都容納著無盡的創造的爆發力。
← 西默農與他的「馬戈探長」 西默農這個人和他的書 讀西默農
【回頁首│回作家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