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敬澤(大陸知名文學評論家,現任《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
山上寧靜的積雪,多麼令我神往!──尼赫魯
1
在《尼赫魯自傳》第六章──《結婚和喜馬拉雅山中的探險》中,尼赫魯寫道:
喀什米爾的高山和山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決定不久就回去遊覽。我定過許多計畫,打算過許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來就使我高興的就是準備去遊歷西藏的名湖瑪納沙天池和附近積雪的凱拉斯山。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去過這兩個地方。甚至喀什米爾我儘管懷念也一直沒有去舊地重遊。我忙於政治和社會活動,走不開。我用坐牢代替爬山渡海以滿足我的遊歷熱。可是我仍然定計劃,這是一種雖然在監獄中也沒有人能禁止的快樂。而且除此之外,在監獄中還有什麼事可做呢?我常常夢想有那麼一天,我漫遊喜馬拉雅山,越過這大山去看望我所嚮往的山和湖,然而年齡不斷增加,青年變成中年,中年以後的時代更壞。有時我想到也許我將要衰老得不能去看凱拉斯山和瑪納沙天池了。這種旅行即使走不到目的地也是值得一試的。
 這些高山出現在我的心頭, 這些高山出現在我的心頭,
山雖然危險,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麼美麗。
山上寧靜的積雪,多麼令我神往!
又過了很多年,我在一個朋友的小說裡讀到了這段話,我從中感到了一種「中年」氣味:到中年,我們終於知道某些事物遠在我們自身的界限之外,比如凱拉斯山和瑪納沙天池。
凱拉斯山即是岡底斯山脈的主峰岡仁欽波雪山,而瑪納沙天池是岡仁欽波附近的瑪旁雍錯聖湖。

2
二○○三年春天,我一直在讀馬麗華的書:《藏北遊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風》和《藏東紅山脈》。
在南京,在俯瞰玄武湖的飯店房間裡,每天晚上看著一場戰爭漸漸臨近,我斷定電視機前所有的人和我一樣,被瑣碎、冗長、註定無意義的延宕拖得疲憊、厭煩。深夜關上電視時,一種邪惡的怒氣猝然湧上心頭:如果它要來,那就快點來吧!
然後,我讀《靈魂像風》,我聽到馬麗華說:
假如我是神,我會使他們如願以償。
回到北京時,戰爭打響,大眾傳媒的盛大狂歡終於正式開始,億萬雙眼睛注視著螢屏,注視著殺戮、背叛、怯懦、愚蠢、傲慢和欺騙,摩西十誡,幾乎每一誡都被公然踐踏,而一切愚行和不義都被「觀賞」,億萬雙眼睛是多麼熱切又是多麼冷漠,「戰爭」填充著我們卑微的日常生活,當它迅速結束時,我們意猶未盡。
與此同時,我讀完了《藏北遊歷》、《西行阿里》、《藏東紅山脈》,我在文字中穿越高山和草原、寺廟和村落,結識農夫、牧人、巫師、僧侶和神祗……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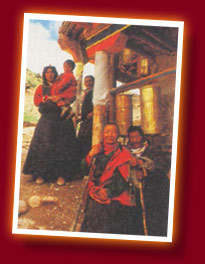 馬麗華屬於一個漫長的人物譜系,這位山東女子1976年二十三歲時進藏,直到二○○三年。她是行走者,是書寫者,儘管她自己很可能不願承認,但她還是一個「發現者」。 馬麗華屬於一個漫長的人物譜系,這位山東女子1976年二十三歲時進藏,直到二○○三年。她是行走者,是書寫者,儘管她自己很可能不願承認,但她還是一個「發現者」。
「發現」,這個詞輝煌而幽暗,其中包含著現代精神的某些根本疑難,「發現」是知識的增進,是理性和進步,是觀察和講述,但「發現」也是一種蠻橫的權力。
對西藏的現代意義的「發現」可以追溯到葡萄牙在印度的傳教士安德拉德神父,他和馬奎斯修士於一六二四年啟程,開始西方對西藏的首次探險,他們抵達了阿里,一路艱苦卓絕。此後三個多世紀,西藏抵禦著紛至遝來的「發現者」,「發現」的一方和「被發現」的一方同樣頑強;在這種對抗中,造物主站在西藏一邊:那裡的自然條件構成了堅固的屏障。
西藏的「發現」史是整個中國的「發現」史的一部分,這個過程伴隨著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規劃,也伴隨著以理性和科學對古老民族的靈魂世界和生活世界進行全面的「去魅」和「啟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山河大地的地理學探測和描述。
一九○七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到岡仁欽波雪山和瑪旁雍錯聖湖,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世界觀中,前者是須彌山,是世界的中心、眾水之源,是眾神居所,而後者是永恆的、洗淨一切罪孽的湖;然而,在《亞洲腹地旅行記》中,我們看到那山那水被斯文·赫定還原為純粹的自然地理現象,籠罩其上的神奇光環被驅散,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在一個以人為中心重新組織起來的世界裡,它們等待著被認識、被征服、被利用。
──這就是「發現」的真義。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後,所有知識份子都是「發現者」。斯文.赫定一九二七年後的歷次考察是在中國知識精英的支持和參與下進行的,其中包括胡適、劉半農這樣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發現」從一種必須防範和抵禦的異己力量逐漸演化成為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內在衝動,「發現者」由早期的外國教士、商人、外交官、軍人和冒險家,轉變為本土的知識份子以至民眾。
二○○○年,我曾參加一次沿黃河行走考察,我的行囊中始終攜帶的一本書是《亞洲腹地旅行記》,在很多地方,我都在尋覓和印證斯文.赫定的足跡,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所做的不過是對斯文.赫定的滑稽模仿。而在《西行阿里》中,馬麗華寫道:
斯文.赫定的旅行和事業總是充滿了艱辛危險。在那曲地區旅行時,我就關注他的行蹤,也處處與他所記述的相印證。為此,我在讚頌自己善良、溫和的同胞的同時,也不得不欽敬那些為了事業甘願吃苦冒險的西方人。我所看到的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隊的專著《西藏地貌》等大書中,還多處沿用了斯文.赫定當年的測量資料。
是啊,不管是否願意,我們得承認,我們是「發現者」譜系中的枝葉。

4
但西藏是中國「發現史」上極為特殊的章節。對中國人來說,它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兩次「發現」,我把兩位女士作為這兩次「發現」的標誌,一位元是馬麗華,另一位是劉曼卿。
一九三○年,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文官處書記官的劉曼卿女士受命隻身赴藏,恢復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聯繫,雖「道路梗阻,積雪沒脛,盜匪充斥,其間屢瀕於危,而女士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排除萬難,卒獲達使命而返」,隨後,著《康藏軺征》一書以志此行。
劉曼卿的父親為世居拉薩的漢人,母親為藏族,一九一一年舉家遷往印度,一九一八年到北京,這年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劉曼卿十九歲。於是,我們在《康藏軺征》中看到的是一個典型的「五四青年」。她的眼光完全是現代的,著意之處在理性、教育、婦女解放、社會發展,她對西藏並無任何浪漫情懷,支持她「排除萬難」的,是五四式的「救亡」激情和英雄氣概。
鑑於劉氏本人有藏族血統,又在西藏度過童年,她的這種姿態尤其耐人尋味。它強烈地預示著中國巨大的現代化進程對西藏的主流認識取向:西藏是前現代的,亟待喚醒和改造,就像整個中國都亟待喚醒和改造一樣。
這種取向一九四九年後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論述中得到了確認和強化: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在歷史進步的階梯上遠遠落後……
──這是第一次「發現」,也是持續至今的「發現」。在《西行阿里》中,馬麗華無意之中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證,同行的一位藏族人類學家,「自小便在母親襟抱裡遠行數千里從康地前往拉薩朝過聖,幼年時便在寺廟裡注過冊,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長大成人」,如今「卻以異乎尋常的冷靜眼光和理性頭腦接納一切見聞」:
這位訓練有素的學者,兀自走得太遠:「子不語怪力亂神」。他就時常認真地批評弟子們的不嚴謹,說我們神神道道,陷入傳說不能自拔。他也進寺廟,也了解傳說,但用的是知性的眼光和耳朵。每每看到漢人和洋人們拜神靈偶像,大大地不以為然:「雪山湖泊本無生命,人們賦予它們靈性罷了。」
──看到此,我不由得想起了斯文.赫定,想起了劉曼卿。
但是,在同一段中,馬麗華還提到了一群「虔誠」的漢人和洋人:
年輕人們的車卻久久不至。後來才知道是月光下的土林迷住了他們,不僅停車欣賞,且舉行了虔誠而浪漫的拜祭儀式,此後每到一寺院一聖地(山,湖,神奇風光),皆如是。非西藏人虔誠起來比之佛教徒猶有過之。不久連南茜教授也屢屢施行跪拜大禮。
──這些人的「虔誠」從何而來?很難想像回到自己的生活後他們會依然如此「虔誠」。

5
第二次「發現」,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有趣的是,這一次的「發現者」主要不是科學家、理論家和政治家,而是文學家和藝術家。
一九八五年,紮西達娃發表短篇小說《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第一次,西藏以神奇的形象進入漢語文學。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正是通過這篇小說,中國人發現了感受西藏的另一種取向:西藏不再被置於進步-落後的客觀歷史邏輯之中,西藏與靈魂有關,它不再是等待改造的物件,而是昭示著神秘浩瀚的可能性。
於是,一個新的西藏被「發現」。如果說,第一次「發現」將西藏納入我們自身,通過科學的和社會歷史的論述,它被合理化為普遍秩序的一部分,那麼現在,西藏又被重新放回了「遠方」──
在陳丹青的繪畫中,對人物和景色的注視隱含著差異性的敏感,畫家和物件之間存在深遠的空間,畫家謹慎、恰當地保持距離,以便玩味這個空間的複雜含義。
這個空間在馬原的小說裡轉化為無窮無盡的敘述圈套,在拉薩縱橫交錯的街巷中,你永遠不會找到真凶、真相或決定性的線索,但是,你始終諦聽著迷宮中心那頭怪獸的喘息。
──西藏成為夢想與遙望與尋覓之地,這種尋覓不是為了印證我們的「有」,而是為了印證我們的「無」。在歷史和時間之外、在難以逾越的高山中倖存的這片地方,成為我們精神上的「異域」。
這種「異域」生成於八十年代生機勃勃的精神氣氛中,它在根本上是對我們自身的開拓和探索:在《繫在皮繩扣上的魂》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馬爾克斯化的西藏,從而「發現」了馬爾克斯式的自我;同樣,在馬原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博爾赫斯式的西藏,也「發現」了博爾赫斯式的自我。
博爾赫斯或者馬原的小說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恐怖,敘述謀殺了事物的實在;八十年代,我們由此驚奇地發現了小說藝術的可能性,但我們同時可能摒棄了事物的溫度、呼吸和生命,敘述成為華美的暴力,它的成功是事物的死亡。
所以,與其說我們通過小說「發現」了西藏,不如說我們發現在西藏便於施用某種文學想像和修辭。馬原至少還在西藏待了幾年,很快我們就意識到,幾年或幾天甚至一天沒有對小說家們並無差別:有位朋友,從未去過西藏,也寫了幾篇西藏故事,據我所知,還真的沒人看出破綻。
──而馬麗華把西藏從宏大敘事和形而上學的玄想中釋放出來,她恢復了、準確地說是建立了一種對西藏的經驗視野,她帶領我們看西藏,看沒有被各種敘述所傷害、所遮蔽的西藏。

6
《藏北遊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風》、《藏東紅山脈》,馬麗華在二十幾年時間裡行於西藏的東西南北,寫下這四本書,一種體驗西藏的新方式由此形成。
早期探險者的動機互有差異:為了傳教、為了商業利益、為了帝國主義擴張,或者像斯文·赫定那樣為了求知,像劉曼卿那樣為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事業;但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他們真的都不太在意自己,他們將一切艱難險阻、一切成功和失敗歸附於某種宏大的意志或意義。
 我曾讀過《韃靼西藏旅行記》,兩位法國傳教士一八四四年從赤峰出發,行經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於一八四六年抵達拉薩,他們盲目、孤獨地穿越陌生的世界,每一步都吉凶莫測;然而,這部書居然寫得如此質樸、超然,似乎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英雄壯舉。 我曾讀過《韃靼西藏旅行記》,兩位法國傳教士一八四四年從赤峰出發,行經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於一八四六年抵達拉薩,他們盲目、孤獨地穿越陌生的世界,每一步都吉凶莫測;然而,這部書居然寫得如此質樸、超然,似乎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英雄壯舉。
還有斯文.赫定,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有眾多的中國仰慕者,他被想像成浪漫的英雄,但是,讀他的書,我所感到的是優雅的自製,他當然是高傲的,但那是被內心深處的尺度感精確平衡著的高傲,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有意義,但這種意義決非止於個人或歸於個人。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次「發現」和第二次「發現」的重大差別,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現」已經不是為了補充、拓展某種外在於我們自身的宏大圖景,「發現」的意義只能在「個人」層面上確證。
馬麗華的四本書提供的就是一種「個人」敘事:
遠行者,一個總是出遠門的人,用了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時光奔波在高天闊地的山野間。是漂泊地,也是歸宿地。五年前的藏東山地牧場,那個冬日的黎明,我們將要踏上歸途。山野冥蒙中,牧民在冬窩子裡為我們燒茶送別。鐵皮爐裡的牛糞火閃亮,映照著一張張如大地如歲月的臉龐。
酥油茶的濃香溢滿了小小的空間,這是前方漫漫長途的最後溫熱,如詩如畫般銘刻在心底了。這詩畫的最後一幕,是曙光微斕中,與那些一生可能僅謀一面的牧民男女們互致祝福揮手告別的情形。
那一刻,我覺得生命中有些什麼正離我而去,永遠地融入了那片凍土地。(〈詩化西藏──《走過西藏》第四版後記〉
在這幅圖景中,處於中心位置的是「我」,這個「遠行者」,她在漂泊,她在漂泊中找到了「歸宿」,而這「歸宿」並非是某種地理、文化或生活事實,而是「生命」,生命因漂泊而如詩。
很難想像斯文.赫定或劉曼卿會這樣自我表述,而馬麗華由此確定了一種新的意義模式,至今盛行不衰。

7
「漂泊」,這是馬麗華的寫作中的關鍵因素,對於西藏的發現史來說,它也是一個新的因素,第一次,人在那片大地上的行走僅僅是為了用身體去經歷,為了身在現場,漂泊本身就是歸宿、就是目的。
在這個時代,通過電視和網路,人間萬象在我們的眼球上清晰映現,我們在千里之外觀看任何一處現場。但儘管如此,身在現場的意義還是非同尋常:我們本能地承認在場者的權威,這種權威來自他們的身體,在一場電視轉播的戰爭中,相對於演播室裡誇誇其談的專家,我們更相信戰地記者,因為他們在那兒,我們相信身體勝過相信任何理念。
當然,我們常常忘了,在場者同樣會一葉障目,會分揀和歪曲事實,他們很可能利用在場的權威施行欺騙,他們會背棄自己的身體:關閉眼睛、皮膚和直覺,讓成見滔滔不絕地向外流瀉。
而馬麗華,用佛家語說,此人有天生的「澄明」,一種直接觸及事實的能力。
很多作家都有這種能力,比如托爾斯泰,他燭照入微,一切浮辭偽飾都逃不過他的法眼,但托氏的能力可謂以天算勝人算,是絕倫大智,而馬麗華的能力則來自罕見的熱情和善良。
讀這四本書,我認識了馬麗華:她是如此熱情,她在熱情鼓蕩下外向--她驚歎地接納眼前的一切,她不是一個縝密、細緻、冷靜的觀察者,相反,她總是很匆忙,這種匆忙不是草率,而是遭到巨大的、繽紛燦爛的景象的轟擊,她在快樂地招架。她的身上澎湃著放任的感性力量,她也思考,她也有觀念和成見,但是,當身在現場,當事物從四面八方撲來,她常常常常忘了思考,她張開她的所有感官喜樂地體會;她是善良的,這不是說她的頭腦裡有鐵一般的道德律條,而是她對人、對事物懷有一種小心翼翼的愛,她惟恐傷害一切,她不忍「批判」,甚至不忍「深思」,因為她本能地覺得任何歸納、演繹、追究和揭破都是對人、對事物極不厚道的侵犯……
人類學家格勒和周星都曾談到馬麗華的「文化相對主義」,認為她的寫作體現了現代文化人類學的這一根本立場,但我認為,馬麗華是一個天生的文化相對主義者,即使她沒有受過有關的學術薰陶她也會是,我寧可把她看成她本來就是的那種人:她是詩人、是文學家,而詩與文學的根本要義就是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將世界從使它乾涸的種種意識形態下解救出來,恢復它的豐滿和複雜。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麗華的漂泊與行走與「生命」有確鑿的關係:遠行者虛懷若谷,她是「空」的,她用身體感受世界的皮膚和溫度,她接納生命的一切可能性,由此,她的生命壯觀、充盈。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麗華標誌出對西藏的第二次發現:斯文·赫定或劉曼卿絕不會像她那樣觀看西藏,他們都是被強大的先在理念所支配的英雄,他們必定有力地篩選和編纂自己的所見;而馬麗華通過她的執著行走,將紮西達娃等人開啟的文學敘述擴張為經驗的盛大狂歡。
於是,幾乎是第一次,漢語世界的讀者直接面對駁雜的、近於真實的西藏:它的神界和人界、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它的可理解和不可理解、它的亙古長存和流動不居……

8
二○○三年的四月,我偶然行經北京的後海,這是一片相對完好地保存了北京舊時風貌的區域。
在這個城市,「現在」正饕餮地吞噬「過去」,後海如同孤島,維繫著我們與前人、與千百年民族生活的聯繫,讓我們感到時間原是有來處、有縱深。
這個春夜,後海正燈紅酒綠,它變得妖冶、曖昧,都市新貴們以混亂、矯飾、自鳴得意的趣味改造著這一地區--經過一間又一間酒吧,我猜想一幢幢房子裡可能多少年前居住著詩人、武士和樸素的百姓,我知道至少其中一間住過郁達夫,一個朋友曾在那酒吧的洗手間裡告訴我:咱們正在郁達夫家裡撒尿。
然後,我在銀錠橋頭看見了「西藏」:巨大的玻璃窗內,琳琅滿目地堆積著西藏風格的傢俱、佛像、面具,木門半掩,門內,明亮的燈光炫耀著一地鵝卵石,它們會不會崴斷了細長的鞋跟?
──來到這酒吧,就來到了西藏?
這時,我想起了馬麗華。我知道,後海岸邊的那間酒吧與馬麗華有關──她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興起的「西藏熱」提供了重要動力。一九九四年,馬麗華將《藏北遊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風》合為《走過西藏》出版,她對這部書的市場效應本不敢心存奢望:「我何嘗不知,這類題材的邊遠,文化情景的隔膜,按以往的經驗它很難進入大眾社會。」(〈詩化西藏──《走過西藏》第四版後記〉
然而,「以往的經驗」失效了,《走進西藏》竟成了暢銷書,某種程度上因為這部書的刺激,「西藏」本身也迅速成為重要的時尚文化元素,到二○○三年,在中國的城市,「西藏」成了飄揚在成功、金錢、欲望和迷茫之上的華美旗幡:誰不曾神往地談論西藏?誰不曾去過西藏或要去西藏?誰沒泡過西藏風格的酒吧?誰沒看過有關西藏的書或雜誌或電視?誰不曾在某個瞬間為對西藏一無所知而自卑?
所有這一切,我無意在此申說,那將是複雜、龐大的論題;我有興趣的是,馬麗華對此作何感想?
是的,馬麗華是善良的,她從來不忍傷害事物,我相信她會像她曾經說過的那樣再說一遍:「國人渴望認識我們的西藏,並由此推進了民族間文化間的了解和交流總是好的;我心目中的西藏由此廣為人知並引起普遍的神往總是好的。」(同上)
但是,當西藏被論述和界定出某種化石般的文化本質,並因此成為一種消費品時,馬麗華在想什麼?

9
在第一次「發現」中,西藏被指認為「落後」,它在第二次「發現」中卻獲得了輝煌的精神光環──馬麗華在《西行阿里》中對那群虔誠者的描述在我看來意味深長:我們來自充分現代化的世界,西藏是我們「發現」和保留的跪拜之地,是我們精神上的公園或後院,我們熱愛西藏,我們熱愛它的方式是希望它永恆不變……
但這是道德的嗎?我們的根本動機不是自私和蠻橫的嗎?在馬麗華的書中,一位美國女士在西藏「什麼也看不見,除了美麗」,這當然是她的自由,但西藏有義務永遠、徹底地向外人、向遊客表現它的「美麗」嗎?該女士還說,「干預和幫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尋求」,話是不錯,但如果你看到的只有「美麗」,你又怎麼能聽到對方是否尋求?當我們企圖把一種文化、一種活生生的民族生活從現代化進程中「保護」起來時,我們是否僅僅為了滿足我們的「美感」?我們難道通過這種方式將西藏在巨大的全球化體系中隔離在被觀賞的地位?
──這些問題很難有清晰的解答,但是,它們肯定暗自困擾著馬麗華。在《靈魂像風》中,馬麗華寫道:
在我回顧描述了仍在延續的傳統人生,記掛著那些悠久歲月中的村莊和寺院,那些人影和音容時,一種憂鬱的心緒漫浸開來。我覺得心疼。覺得不忍和不堪。從什麼時候開始,一種不自覺的意念從腦海深處漸漸上升,漸漸明晰。浮現於海面,並漸漸強化起來。我凝視著它--這是對什麼的不以為然。
不是對於生活本身,人群本身,不是對於勞作者和歌舞者,甚至也不是對於宗教。
是對於靈魂和來世的質疑吧--是,或者也不儘然。
靈魂和來世的觀念盡可以存在,與基督和伊斯蘭的天堂地獄並存於觀念世界。
只是,靈魂和來世觀念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如此左右著一個社會和世代人生,則令人輾轉反側地憂慮不安。
──誰從中獲益?
──老百姓本來可以過得更好一些。
──人生,造物主恩賜於人的多麼偉大、豐盛的貴重禮品,你其實只有一次生命。縱然果真有來世,也應該把今生看作是僅有的一次。
──缺乏的是一次人本主義的文藝復興。
在理論上提出和展開問題並非馬麗華所長,我完全可以逐條反駁她的疑問,而且我自信可以巧舌如簧,說得漂亮;但她的猶豫和誠懇使我感到虛弱:我知道我的巧辯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但馬麗華卻必須負責任,當她提出疑問時,她是「西藏的馬麗華」,她已經把青春、把大部分生命交給了那片土地和人民,她的疑問也是針對自身的反詰。
《靈魂像風》因此成為這四部書中最具深度的一部,馬麗華揭開了西藏的光環之下真實的躁動和困境,在這部書中,她無意中呼應了先行者劉曼卿的聲音。
是的,老問題至今仍在,它被馬麗華、被那位「不語怪力亂神」的藏族學者從西藏的內部深切地體會著。
儘管取向不同,但第一次「發現」和第二次「發現」同樣源于我們的現代性衝動和焦慮,正是第一次引發了第二次,「西藏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興起,只有在中國巨大的市場化浪潮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這是我們在「進步」的道路上高歌猛進時對自己作出的文化補償,這種補償本就預設在現代精神之中。
那麼,西藏呢?難道西藏應該成為這種文化上的補償品?
西藏一直是孤獨的,馬麗華也是孤獨的。這個以漂泊為歸宿的人最終發現,即使在西藏,人也無法安頓自己的靈魂:
深夜擁被獨坐。腦海和心懷一派空虛。突然間,一個念頭不期而至--
你何時才能結束心靈的流浪?(《靈魂像風》)
--這時,她是否看出了我們所有的人:嚮往西藏的人、前往西藏的旅遊者和跪拜者,我們心中深藏的不可救藥的空虛和自欺?

10
於是──
西藏的高山和山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決定不久就去遊覽。我定過許多計畫,打算過許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來就使我高興的就是準備去遊歷西藏的名湖瑪旁雍錯和附近積雪的岡仁欽波山。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去過這兩個地方。甚至西藏我儘管嚮往也一直沒有去成。我忙於工作、賺錢、看電視以及生兒育女,走不開。我用日復一日的生活代替爬山渡海以滿足我的遊歷熱。可是我仍然定計劃,這是一種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人能禁止的快樂。我常常夢想有那麼一天,我漫遊喜馬拉雅山,越過這大山去看望我所嚮往的山和湖,然而年齡不斷增加,青年變成中年,中年以後的時代更壞。有時我想到也許我將要衰老得不能去看岡仁欽波和瑪旁雍錯了。這種旅行即使走不到目的地也是值得一試的。
這些高山出現在我的心頭,山雖然危險,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麼美麗。
山上寧靜的積雪,多麼令我神往!
|







 這些高山出現在我的心頭,
這些高山出現在我的心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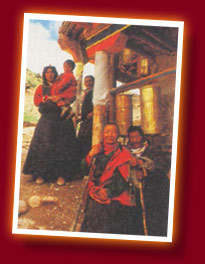 馬麗華屬於一個漫長的人物譜系,這位山東女子1976年二十三歲時進藏,直到二○○三年。她是行走者,是書寫者,儘管她自己很可能不願承認,但她還是一個「發現者」。
馬麗華屬於一個漫長的人物譜系,這位山東女子1976年二十三歲時進藏,直到二○○三年。她是行走者,是書寫者,儘管她自己很可能不願承認,但她還是一個「發現者」。 我曾讀過《韃靼西藏旅行記》,兩位法國傳教士一八四四年從赤峰出發,行經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於一八四六年抵達拉薩,他們盲目、孤獨地穿越陌生的世界,每一步都吉凶莫測;然而,這部書居然寫得如此質樸、超然,似乎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英雄壯舉。
我曾讀過《韃靼西藏旅行記》,兩位法國傳教士一八四四年從赤峰出發,行經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於一八四六年抵達拉薩,他們盲目、孤獨地穿越陌生的世界,每一步都吉凶莫測;然而,這部書居然寫得如此質樸、超然,似乎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英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