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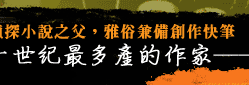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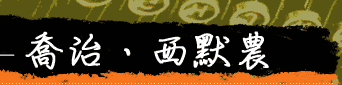

天真狀態的告終 文/盧郁佳
|
這位鄉紳的老光棍生活,不失為讀書人的避世桃源,可是在親友眼中卻顯得病態。問題不在於他髒亂、酗酒或自私,而是在他的環境當中,這樣孤僻是不道德的。親戚的譴責,意味著每個人各有該待的位置,透過關係與訊息互相連結來維持,而俱樂部統治這一切。鄉紳發現自己是法院橋牌俱樂部的成員,該會網羅本市的所有顯貴,為審核新貴入會而熱烈爭論,是否躋身上流社會要靠他們說了算。而那些百無聊賴的年輕人,則在最寒傖的妓寮和酒吧裡結黨呼嘯。 但這裡有點不顯眼的出軌。為了一種匪幫式的想像,富家兒女和窮小子忽然混在一塊兒了。儘管窮小子當差幹活時、只能眼巴巴乾望著富家子瀟灑上學去,但在夜晚共享放肆歡娛的氛圍,彷彿便跨越了界線,貧富階級有了縱向的交情。
西默農的偵探小說,常常像《後窗》,出在公寓裡的雞犬相聞謀殺案。美國冷硬派辦案,多聚焦於受害者在城裡星羅棋布的人際關係;他卻專找鄰居,挨家挨戶盤查下去,最後地緣關係居然也就真的是人際關係。這些故事描繪出一個盤根錯節的老國家,年深月久的老鄉里。法國電影裡常見的公寓意象,都不如西默農小說把它的文化意義說得這麼明。 美國片裡,公寓單位是橫向排列,由甬道連結起來的。旅館走廊般空盪無人,房間沒有名字,誰也不相識。 法國片裡,公寓單位是垂直堆積,由階梯連結起來的。鄰居在鑰匙孔眼裡窺望,等著開門聊是非:先後來訪的男友,在樓梯上錯身交瞥;女人俯憑螺旋階梯,叫住天井裡的誰。 甬道公寓是美國曠瀚公路的縮影,加油站、餐館、小鎮,星散錯落在道旁,和最近的鄰舍相距數百哩。而且很可能,城市同層樓的住戶就來自那些小鎮,他們遂像彼此的故鄉般各自生滅,互不相擾。 階梯公寓是法國舊日雜院的立體化,每個人得經過每扇門,屋裡一跺腳樓下就敲門,從水管到天花板,樣樣聲息相通(想想尚皮耶,從《黑店狂想曲》到《愛蜜莉的異想世界》都以公寓的縱向關係為主角)。 美國移民社會向有白手起家的神話,外來者、新居民夢想隱藏自己的出身。這種題材永遠吸引他們,《羅馬假期》公主扮平民,《窈窕淑女》平民扮公主,一直到《成功的秘密》或《麻雀變鳳凰》,傳達的訊息是:一切始於偽裝,如果裝得夠像,你就成為這個階級。聽來像是基督的福音一樣:人皆有可能平等,因為偽裝是完全可能的。 西默農會告訴你,在法國,不可能。
法國社會,階級分明一望而知,就像住在階梯公寓裡,他們隨時都知道頭上頂的、腳下踩的是什麼人。每個人認識每個人,即使不認識,也認識他腳上的皮鞋。敘述者總會先從衣著態度、皮鞋剪裁是否上乘,來判斷登場角色的背景。這對偵探來說算是不錯的開始,因為一個人的階級,往往就是他的困境。因此一幢公寓裡,這麼堆積起來的一點點階級差距,便成就了無窮煩惱與曲折傳奇。 他那麼多可視為鄰居恩仇的公寓小說裡,《屋裡的陌生人》反其道而行。鄉紳即使在家裡也是異鄉陌客,像入獄多年與社會脫節的囚犯,當他走出去,試著把現況和認知連起來,對劇烈落差感到一陣陣不適應的刺痛。他自己原本模糊滲開在私房小天地裡,現在環境和自我的界線清晰對焦了,「生平頭一回,他是意識到他在那兒,他是盧爾薩,四十八歲,這麼的厚重、滿臉鬍腮,還有,這麼的髒!」原本存而不論的一切,隨之慢慢顯明。自囚的歲月使他產生了必要的疏離,在重新審視原生脈絡時,終於認出了習以為常文化體制的血腥之處。 這是鄉紳的甦醒,也是青年們的甦醒。窮小子和富家子一起找樂子,老一輩便知道這事不長久,情義相契當中已經埋藏了身分衝突。作者安排跨階級友誼的存在,只是為了揭露關係的內蘊,演示階級傾軋的慘烈。過去沒有明講的,貧富彼此的偏見,一個階級的文化習慣在另一個階級怎樣形成死罪,凡此種種,都在法庭上直擊要害。 在那些公寓小說裡,階級是必要的配角;而在穴熊盧爾薩的冒險當中,階級才成為主角。 凡有三個人聚會,惡魔必臨到他們中間 西默農經常處理男性結黨文化的題材,一群小夥子為著時髦的思想而獻身焚燒,青春被燒盡的人無法原諒未被燒盡的。圈子裡遊戲似的小小結盟與對立,在危機變得尖銳時,轉為推諉與陷害。若問西默農憑什麼比《是誰搞的鬼》之類尖叫片來得深刻,所憑藉者是他深知青春的無助,亟需寄託於教條或社群,急於加入某個俱樂部,因不足為外人道的召喚,而奉獻自己手中的一切。 無論哪一種理想,如果它沒有出賣過你,那就不叫理想。 在這一點上,《屋裡的陌生人》遂成為悼亡之歌,為被青春深深傷害過的那群人而繼續演奏。天真一定都結束得太遲,但遲到總好過不到。為了讓人生不再繼續詐欺我們,總是有人必須叫停。奇妙的是,總等有人死了才會真正喊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