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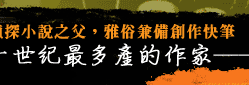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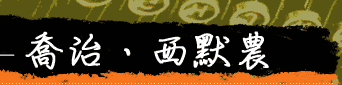

愛像一條狗 文/盧郁佳
|
西默農的《黃狗》正是這樣的故事,最初人們像在伊甸園裡般純真安樂,繼之而來的是雙重出賣、徹底剝削與背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如何度過殘生,以及永不忘記這一切的狗再度降臨。牠來自地獄,一旦牠咬住什麼,就是死咬不放。 這隻死過一次的狗,像幽靈般出現在所有案發地點:週末深夜的海港,肥胖的酒商走出旅館,中槍倒在路上;接著旅館的餐酒裡有人下了毒;一封預知凶案的黑函寄到了報社。 「康卡爾諾最後一群快樂的小伙子」似乎一個個面臨死亡威脅,本埠人人自危,興起了獵巫般的集體狂熱,居民與警方開始圍捕這條野狗,與在現場留下神秘大腳印的怪人。 這條猥瑣、馴順而沈默的狗,在群眾眼裡,已經成了巴斯克維爾獵犬的化身。
柯南•道爾的《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往年劣紳土霸巴斯克維爾強搶民女,派出狗群追嗅逃逸的新娘。惡黨在叢莽間連夜搜索,最後只見一頭龐然大物,在黑暗中狺狺然低嗚。巨犬咬斷了巴斯克維爾的喉嚨,就此消失,留下無盡的傳說。到了福爾摩斯的時代,傳說再度復活了,並且大開殺戒。 然而神話與底蘊總有落差,就像無頭騎士可能只是一具梟首的死屍,由人綁在馬背上奔走,這是版本之一。小說《瞌睡谷的傳說》改編成電影《斷頭谷》,又是另個版本,把一則半明半昧的鄉野奇談,續補為獵巫的時代寓言。偵探小說做的似乎就是這種工作:替近乎超自然、不可能發生的怪案,添寫下半截,給一個合理的動機和過程。這一筆可以點石成金,也可以讓神話頓時腐朽、灰飛煙滅。《黃狗》顯然屬於前者,作者在巴斯克維爾獵犬式的恐怖陰影中,獨獨看出了一個愛情故事,像費里尼《大路》大力士與智障女的,天真、美麗、悲慘的愛情故事。電影裡的智障女,像一條狗尾隨著主人,即使終於給拋下了,她的歌謠依舊繚繞在風中,在某個早晨追上了旅人。以致他循聲而去,問唱著歌晾被單的婦人,在哪裡遇見過那女的。婦人說,噢,她已死了。西默農把這關係稍微挪動角度易了位,打個圓場,但仍不改其狗也似的悲慘作踐與潦倒癡心。 西默農的結尾,非要告訴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他處理犯罪,態度之成熟,實在無須贅這麼一筆。可能有人說是通俗劇作風,討好小市民讀者;但我相信,那是因為故事裡有顆狗一般的心。單純信仰世界如恆,因此對異樣動靜高度警覺,立刻豎起耳朵、掀翻背毛,一定要弄清楚怎麼回事,並且擺平它,而最終滿足於安穩恬淡,萬物各歸其位,牠可以枕在前爪上繼續打瞌睡。 但若只具備狗的心,小說家僅能成為獵捕者、審判者、行刑者。上帝的獵犬,福爾摩斯,他的志業與其說是揭發罪犯,倒不如說是揭發他自己超越於罪犯與受害人之上、近乎神的存在。證明自己是如此全知全能之後,他便拋下這些無機的受造物,胃口大開地迎接慶功宴。他沒有憐憫,沒有同理心,因為他的成功建立在抓人小辮子上頭。狗屬於色盲,非善即惡,黑白二分,沒有高倍縮放瞳孔、微妙感知的能力,貓的能力。貓,不置可否,哀矜勿喜,敏感多疑的巡行者、觀察者、逃逸者。
阿嘉莎•克莉絲蒂的《鴿群裡的貓》,師生紛紛回到貴族女校開學,但是鴿群裡混進了一隻貓,有人冒充身分夾在裡邊,讀者得找出其中蹊蹺。事情經常如此,遠方親友來訪、或突如其來的遺產,驚動了平靜小鎮,接著就是連續凶案。原來熟識的圈子裡居然有人是冒充的,且偽裝了好多年。為了避免暴露身分,他動手逐一謀殺接近真相的人們。這種狀況之頻繁,連她筆下的神探白羅,也要把核實身份列為辦案初步,先排除假冒的嫌疑,免得書迷老在這上頭瞎猜。 看,偵探小說分為狗與貓兩種。 狗的偵探小說,就如柯南•道爾,常始於一樁不可能的怪案。例如密室謀殺,敘述思維執迷於離奇的煙幕、詭異的凶器、邏輯的正反推演(恰巧是《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黃狗》當中狗所扮演的角色),故佈疑陣,借刀殺人,暗渡陳倉。故事止於正義獲伸張,罪惡有了抵償。 貓的偵探小說,就像阿嘉莎•克莉絲蒂,常始於寧靜的日常生活。一樁看似平凡的凶案,早有了現成解釋。需要世故多疑的老太太,或直覺異樣的當事人,忽然犯了傻勁來翻案。好比東西放在貓跟前,牠懶得理;要是藏在地毯下露出小半截,牠瘋了也要扒出來。角色是一批小報讀者樣的人物,永遠記得多年前聽過的醜事,對隱私有難以饜足的好奇心,線索常來自他們不吝偷窺、竊聽,搬弄是非,掠奪和私藏證物。就像走過牆頭的貓,看盡千家萬戶窗眼裡的秘密。 貓偵探雖然有個好理由去辦案,但從他的行為看來,與其說要破案,倒不如說想落實旁人偽裝下的本相,也就是說:這種偵探對真相的熱情,跟媒人想確定相親對象的品行,兩者是等值的。 正義固然重要,但沒那麼重要,因為偵探以一隻貓的睿智,明白審判無法叫事情回到原點。死者不可復生,而傷害早在謀殺之前很久很久就已鑄成。哀傷如此之深,連謀殺都僅能作為對它的一種表述,你還能說什麼。死刑不能救贖、也不能啟蒙凶手。悲劇不會停止、只會擴散。在一個無可救藥的世界裡,偵探僅能欲求真相,但從不抱持幻想。 貓類小說的力道,不在於真相匪夷所思,而在於角度的穿透力。講到這種角度的強大,犯罪小說《雪上污痕》裡,受害少女逃脫,懸疑高潮之際,西默農筆鋒一轉,慢慢講起行凶少年的回憶。 他幼時看過貓被狗追到樹上,眾人哄誘,卻只讓牠逃得更高、更絕望,甚至有人提議去拿槍。那不是村裡的貓,遍身血污,一邊眼球掛在眼眶外,人人看了都想吐。牠在樹梢整天慘叫,第三天沒了。他永遠不曉得結果怎麼了。這時他想起貓,少女就是那隻貓。 我真是驚歎啊。作者言盡於此,但態度完全表達了。這世界每天都在無謂地輾壓、傷毀,並不白費心思去多想結果,結果的不可逆轉,結果的驚狂傷痛,這些都不考慮,而且有時世界就是我和你。這就是犯罪。 貓總是喜歡在高處俯瞰。牠疏離地注視整個景觀,看得既深且遠。 因此當牠對著整座城市徹夜嚎叫時,我總相信貓在為這個世界而哭泣。
我想說,西默農用狗的心寫偵探小說,用貓的心寫犯罪小說。但作家不真的受分類所限,西默農也是。他的偵探小說裡有狗的熱血正義,但也有貓的惡作劇試探、尷尬的失手、力保顏面的偽裝與追查。他具備小市民道德的溫情,卻不侷限於這種溫情。 跟隨他追跡凶手之際,你若願注意一下偵探的腳印,有時那是狗的,有時是貓的印子。如果第一眼認定他改不了就是個狗脾氣,或肯定是陷在貓的身段裡,說真的讀者很容易低估了他。他的文字出於通俗,毫無雕琢,因此第一遍掠眼常常也就看漏了某些事的強烈暗喻。再讀一趟結尾,看他解釋熟人為什麼認不出那條狗,口氣是這麼平常,就好像自己也沒意識到這事的份量。很多時候,這麼 如果你猜到了他的秘密,我想,他就是在兩種腳印交錯的時刻震撼人心。 (註)捕物帳:捕快時代劇,類似「事件簿」。 |
